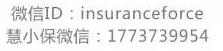渤海人寿风险处置再进一步:注资、换帅、迁址,打响艰难重生之战公司动态
从“海航系”的重要成员到天津国资接手的亏损险企,从“狂飙突进”到偃旗息鼓,渤海人寿的十年沉浮成为了一批问题险企的缩影。
近日,这家公司动态频繁。人事上,监管老将寇江华获批出任董事长职位,同时还在通过市场化手段招聘两名副总经理;资金上,公司表示,去年增资10亿的天津国资未来还有进一步的注资计划。此外,在今年9月,该公司还将总部由天津市中心的赛顿中心迁至20公里外的空港经济区。
种种消息之下,渤海人寿面临的是一场更为艰巨的重生之战:累计亏损近百亿、偿付能力迫近监管红线、风险评级连续十几个季度为C类……要解决数年来积累的沉疴旧疾,虽不能指望毕其功于一役,但也需要掌舵人有相当大的魄力。
老将出马,总部迁址,渤海人寿风险处置开启新阶段
2024年末天津国资的首轮10亿元增资,标志着渤海人寿正式进入地方国资主导的新阶段,为这家“暴雷”之后深陷亏损泥潭的险企提供了喘息之机。
治理结构重塑同步展开。2025年9月,寇江华接替超龄退休的吕英博,正式出任渤海人寿董事长,并兼任公司临时负责人。这位新的掌舵人今年49岁,拥有经济学硕士研究生学历,属科班出身,并具备18年金融监管经验。
自2000年8月进入原中国保监会工作以来,他在办公厅和消费者权益保护局等多个部门任职,从科员起步,逐步晋升至副主任、处长等职务,其中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方面的监管工作经历就有6年以上。
2015年至2017年期间,寇江华挂职天津市滨海新区中心商务区管委会副主任,2018年4月开始主职天津港保税区管委会副巡视员。之后寇江华还曾担任多个相关职务,包括天津市滨海新区金融工作局党组书记、局长,以及中国(天津)自贸区管委会办公室党组成员、副主任等。
与寇江华上任同步,渤海人寿还启动了悬置数年的总经理选聘程序,并推行高管选聘市场化,面向社会公开选聘两名副总经理。据悉,目前高管选聘工作已进入候选人甄选阶段。
与此同时,渤海人寿将总部迁址至天津空港经济区。官方给出的表述是,利用当地的政策与区位优势,通过战略协同、业务协同和资源协同,积极开拓特色业务领域。或许可以期待,渤海人寿在航空旅客意外伤害险、企业团险等产品创新上有一些亮眼的表现。
此外,渤海人寿也表示,继去年投资10亿之后,天津国资仍有继续注资的计划。但不论注资规模如何、何时到账,险企都应当极力避免“拿钱填坑”的思维误区,而是要将资金作为企业“造血”的原材料,让资金发挥杠杆作用,撬动企业的发展。
狂飙突进时代落幕,收拾残局并非易事
渤海人寿的故事始于2014年12月,作为首家注册于天津自贸区的寿险公司,如果说它的诞生如同一颗新星冉冉升起,那么回顾其近些年的历程,则更像是一场激进投资下的不断坠落。
成立之初,渤海人寿凭借万能险等短期理财险业务快速做大规模,总保费从2015年的33亿元猛增至2016年的185亿元。更引人瞩目的是,它打破了行业“七平八盈”的定律,在成立的第二年就实现盈利。
但这种辉煌背后隐藏着致命隐患。海航系的入主让渤海人寿逐渐沦为“提款机”。公开资料显示,2016年至2017年,渤海人寿共有5笔、合计16.17亿元资金流向“海航系”,且未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
随着2017年海航集团陷入流动性危机,渤海人寿的潜在风险全面爆发。2018年,公司净利润由盈转亏,当年亏损达7.68亿元。此后亏损窟窿越来越大,至2023年间已扩大至31.01亿元,六年间合计亏损92.64亿元。
股权问题同样棘手。2023年第四季度偿付能力报告显示,渤海人寿13家股东的股权处于质押或冻结状态,合计占总股本的68.14%。这种股权结构导致公司治理长期失灵,决策效率低下。
2024年末,天津地方国资入场,渤海人寿迎来发展新阶段,但国资入场并不意味着渤海人寿万事大吉。相反,该公司正面临多重挑战,任何一项都可能成为压垮它的最后一根稻草。
现金流压力是当务之急。尽管天津国资注资10亿元,但相对于渤海人寿的巨额亏损和资产减值,这笔资金只能起到过渡性缓解的作用。同时,过去依赖的万能险业务大幅收缩,而保障型产品的开拓需要时间积累。在保险主业青黄不接的背景下,渤海人寿的投资收益也因历史包袱而难以提升。
人才流失风险同样不容忽视。总部迁址在“利用区位和政策优势”“顺应打造高端产业聚集区需要”的同时,也要付出相应的代价。据悉,由于新地址位置较偏,一些员工不愿忍受通勤痛苦,已经选择离职。
此外,作为海航系“负面遗产”的一部分,渤海人寿亦有诉讼缠身。2025年6月,渤海人寿被天津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连带执行近2亿元。
此外,公司还涉及多起巨额未决诉讼。
投资纠纷方面,其与西藏金融租赁等公司的纠纷标的额达6.37亿元;与永泰房地产等公司的纠纷标的额达6.69亿元;与金世旗国际控股等公司的案件标的额更高达12.56亿元。存款纠纷方面,其与浙江稠州商业银行的多起案件,单案标的额从2.63亿元到5.62亿元不等。
渤海人寿的案例已成为观察中国保险业风险处置的重要样本。从曾经的“开业即盈利”到连续六年巨额亏损,从资产驱动负债的激进扩张到国资主导的化险改革,这家险企的十年沉浮是许多中小险企发展的缩影。
近年来,百年人寿、信泰人寿、亚太财险、恒大人寿等问题险企在经历危机后,都陆续迎来了地方国资股东。这一模式逐渐成型,反映出监管层面在保险业风险处置上的策略转变。
天津国资的入场为渤海人寿提供了重生机会,但绝非无限兜底的保证。真正的考验在于:如何平衡风险处置与业务发展?如何在补齐历史欠账的同时谋划未来?如何在国资主导下保持市场活力?
对于渤海人寿而言,脱离“海航系”只是第一步。接下来,它需要在业务结构、资产质量、人才队伍等方面进行全方位重构。这个过程注定漫长且充满挑战,但其成败将为中国众多问题险企的风险处置提供重要借鉴。
保险业的竞争格局正在重塑,过去那种依靠激进投资、快速做大规模的时代已经终结。渤海人寿能否借助国资背景拾起服务用户的初心,能否在补齐偿付能力短板的同时重塑核心竞争力,将决定它能否真正实现重生。